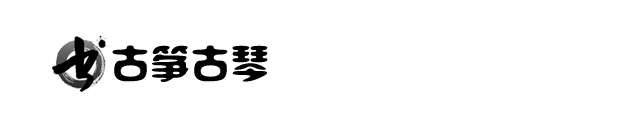她是被失婚之痛所困的平凡女子,他是下挺身而出的英勇武士,本无交集的二人,却因一场樱花树下的短暂邂逅,编织起了羁绊一生的姻缘…片中并无多语,两场山樱的花开花落就诉尽了为爱情相守的真挚与纯粹。
在那个人人身不由己的战乱岁月里,身为武士的手冢背负着太多的责任与使命,而这些壮志豪情在遇见野江的那一刻却似乎都被抛之于脑后。只一支为她而折的粉樱,这位沙场将士心中最柔软的一面便被悄然呈现。
回望这段延续了数百年的“武士时代”,遍山烂漫的樱花或许见证过太多的离别与等候。而正如手冢摘下的那支折樱,在刀剑打杀的外衣裹挟下,这一独特社会阶级的出现,也曾为东瀛传统美学的缔造提供过太多的灵感与契机。
从文学绘画到工艺美术,武士形象所衍生出的创作主题与社会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古时的日本艺术发展。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便要属后来曾一度风靡于西方,甚至至今仍旧热度不减的「芝山镶嵌」工艺。
“芝山镶嵌”也被称为“芝山象嵌”,是一种由江户时代杂货商大野木专藏开启的象牙镶嵌技法,又因其起源于如今的千叶县芝山地区而得来此名。作为曾令日本走向世界的王牌法宝,当中更包含着堪称极致的精细手工艺和高度装饰性。
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现藏于日本宫内厅正仓院 / 自中国而来的螺钿工艺经本土发展,造就芝山镶嵌技法
这种奢华考究的东瀛传统工艺通常以珍稀贝类、珊瑚、玳瑁等天然原料为材,并以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刻画出呈现立体质感的花鸟及人物纹饰,再施以金、银、铜等华色,加之极其繁复的镶嵌技术的加工才得以最终完成。
或许如今的我们欣赏着小盒、花瓶亦或是多宝阁上繁美旖丽的芝山镶嵌装饰时,并无法想象美貌的它与武士有何关系,但实则这一工艺的诞生便是因「武器」而起。
左:约1885年日本造公鸡主题芝山镶嵌描金箪笥,V&A藏 / 右:1850年代日本造芝山镶嵌工艺印笼,V&A藏
在江户时代,随着社会的逐步安定,武士阶层便开始关注起日常所佩刀具的艺术美化,这一风潮的盛行更使得刀具中“锷(即护手或剑格)”的装饰得到了大肆发展。而芝山镶嵌技法最初就正是被用于此类精美的随身利器之上。
但随着此后明治时期武士阶层的衰落以及废刀令的颁发,这种精湛的刀具装饰工艺才转而被运用到香炉、屏风、漆器等其他艺术作品上。而谈及芝山镶嵌的黄金时期,18-19世纪,一股火遍欧陆的日本热潮则是不得不提起的“幕后推手”。
18世纪,随着“时尚风向标”玛丽王后一同进入凡尔赛宫的,还有数件来自遥远东瀛的奇珍异宝,自那时起,这抹异域风情便凭借令世人叹服的精工将各国征服。芝山镶嵌动人的熠熠华光更成为皇室贵族尤为偏爱的东国工艺。
在那个以奢华之风著称的洛可可时代,繁美的芝山镶嵌技法赋予了欧陆匠人用之不竭的灵感。一时间,同样以珍贵贝类为材的镶嵌工艺开始盛行于整个宫廷,在东西方还尚无法“相见”的岁月里,给予西人以无限的日式遐想。
18世纪皇家工匠Franz Zeller出品紫檀木嵌珍珠母写字桌,灵感便自东瀛工艺而来 / 德国卡尔·菲利普三世委托制作
金地屏风、黑漆多宝阁、日本花瓶乃至身着和服的玩偶,都是19世纪上流阶层展示财力地位的标配
直至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日本代表团的出现,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贸易的开放,这些“正版”芝山镶嵌作品才终得以漂洋过海,映入大众眼帘。富有立体感的雕造与各类珍材所折射的奇色,更令其拥有了「东方马赛克」之美誉。
19世纪奥地利画家Max Schödl笔下的各式东瀛雅器,芝山镶嵌桌屏更是画面焦点
在机械化生产早已成为日常的今天,回看这些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够完成的芝山镶嵌艺术品,似乎更能被当中所蕴含的匠人精神所折服。每一块嵌片的精妙处理,也都是对其为何至今仍能在收藏界“加冕”的最佳佐证。
两件芝山镶嵌老鹰及公鸡造型嵌片制作的展示 / 每一片羽毛都是对工匠的极致考验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